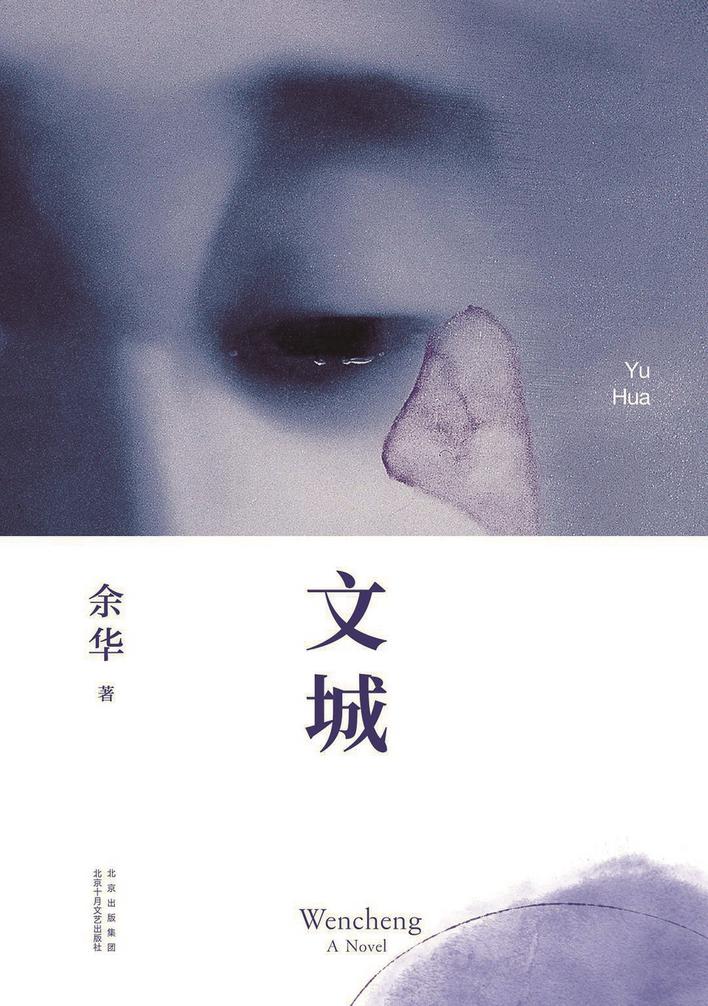□ 涂启智
读完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我不禁内心一声长叹。
林祥福、陈永良、李美莲、田大、顾益民,阿强、小美、小美的婆婆等人物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们心地善良,命运却分外坎坷;怀抱热切希望,但饱受摧残身不由己;奋力抗争,却遭受魔咒般逃不脱苦难劫数……掩卷思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即是黎民百姓、芸芸众生的无上幸福。
《文城》以林祥福和纪小美的凄美故事为主线,多维度描述与两位主人公牵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故事有着强烈的悲剧幻灭色彩。“文城”并不存在,林祥福不可能找到。他寻找“文城”,只是为了寻找小美。在溪镇,他其实已经接近小美。但“宿命”让他与她失之交臂。
“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林祥福后半生的美好就是与小美夫妻团聚。但是,这种愿望注定无法实现,小美在认识他之前,已经嫁给阿强,两人恩爱有加。阴差阳错造就林祥福与小美的“孽缘”,转瞬消失了踪影,成为林祥福生命中的“水月镜花”。
林祥福从父亲手中继承厚实家业,却丝毫没有挥霍游荡习气,而是不断将家业发扬光大。他是一个能成大事之人。历经磨难,仍不失淳朴,始终相信美好,总是把人和事往好的方面想,见证他的乐观与坚韧。为了营救溪镇商会会长、民团团长顾益民,他主动只身前往土匪窝,这是大勇。他为女儿林百家所做的一切,见证“怜子如何不丈夫”。“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后来成了万亩荡和木器社的主人,林祥福身上的谦卑和沉默依旧未变。
林祥福深入骨子里的善良天性,从他对待小美的态度可见一斑。小美第一次离开他,卷走七根“大黄鱼”和一根“小黄鱼”。当小美返回林祥福身边,没有带回一根金条。林祥福并未怪罪她,也不问金条去处——他仍然幻想着与小美共度此生。
林祥福的人格与形象近乎完美。他越是完美,结局的悲惨就越让读者感到分外凄凉。
书中许多人物身上都闪耀高贵的人性光芒。当初,陈永良义不容辞收留落难的林祥福父女。后来,林祥福死在土匪张一斧刀下。陈永良与土匪斗智斗勇,近身肉搏,最终“将尖刀还给张一斧”,为林祥福报仇雪恨。这是陈永良的善良、勇敢与仁义。田大兄弟尽心尽力为林祥福看管家产,林祥福说将田地产出归他们兄弟所有,但他们执意将所有产出折成现银,原封不动交给林祥福。为了接林祥福叶落归根,田大客死路途。这是他们兄弟的忠诚与仁义。
即便是阿强与小美,所作所为包括对林祥福的伤害,也终归出于善良初衷。阿强不愿意小美跟他一起继续受苦,对林祥福谎称他们是兄妹,让小美留在林祥福家。小美想到阿强到处流浪,于心不忍,不惜铤而走险,偷走林祥福的金条,去寻找阿强。当她发现自己怀上林祥福骨肉时,又义无反顾返回,为林祥福生下女儿后再次出走,从此一去不返。
林祥福多年后死于土匪暴乱,几个仆人送他北上归乡安葬。中途歇息,灵柩正好在小美和阿强的坟墓旁边停留。林祥福苦苦寻找小美二十年,“相逢”竟是如此惨烈。此时,距离小美在雪灾中冻死已经过去十七年。此情此景令人悲从中来,肝肠寸断。
林祥福、小美、阿强之间的复杂情感,林祥福与小美的爱情悲剧以及苦难生活缘起,直接推手可以说是小美的婆婆。这个脑子里充斥封建家长制观念与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女人,面对小美偷偷接济娘家弟弟、阿强和他父亲竟然都向着小美说话“接济自家弟弟不算盗窃”,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尊严受到损伤,一纸休书将小美打发回娘家。三个月后,阿强离家,带上小美私奔……
有些悖论的是,小美的婆婆临终之际,嘴里一直喊着小美,不断催促阿强的父亲让小美过来,她要把账簿亲手交给小美。小美的婆婆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军阀混战、匪祸泛滥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底色。
余华擅长从恢宏视野展开苦难叙事。那些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缠绵幽怨……都在其笔下徐徐展开。读者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小说叙事的洪流依然不管不顾,披荆斩棘,一路向前。
《文城》也有叫人费解或瑕疵之处。林祥福在大雪中重返溪镇,小美尽管躲着不见,但心疼女儿,托保姆将婴儿衣服和鞋子交给林祥福。林祥福最后想清楚保姆所说话“给小人穿!”他也联想到小美当年习惯将婴幼儿称为“小人”。我以为情节就此峰回路转,林祥福因此想到小美就在附近。
可惜,作者却将笔墨荡漾开去——林祥福想到是不是这家也有小孩,甚至猜想是否这家孩子夭折——就是不朝小美的蛛丝马迹上去联想。难道小美的针线手工他都忘记了吗?林祥福在溪镇居住二十年,一直在寻找小美。虽然小美与阿强很早就在雪灾中冻死,但他们毕竟也在溪镇居住数年,偏偏他们两人事情始终无人向林祥福提起。这不免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