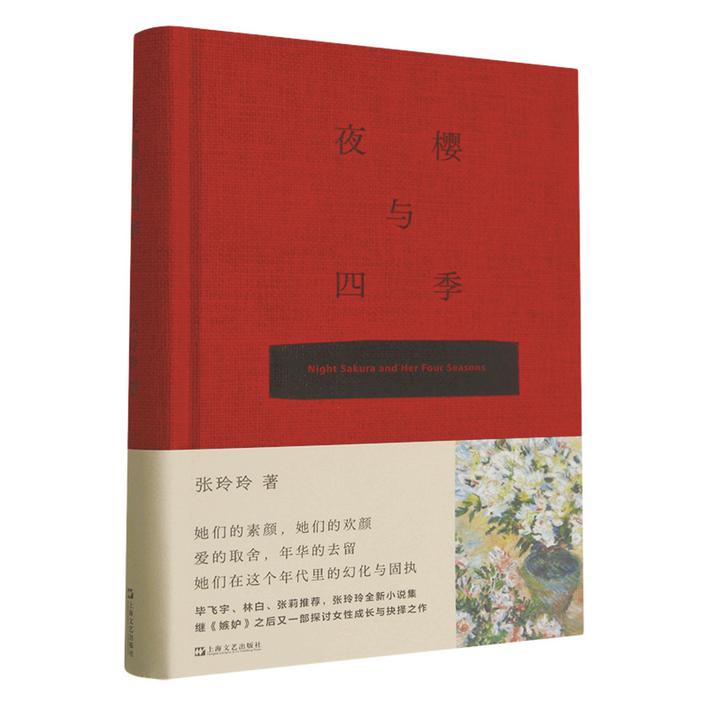□ 孙功俊
《夜樱与四季》是张玲玲继《嫉妒》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收录了她创作的《夜樱》《奥德赛之妻》《洄游》《四季歌》等七部作品。从江边小镇、海岸渔村、不同城市再到大洋彼岸的漂泊足迹,聚焦成人世界里关于自我讲述与真实之间的晦暗地带,通过在现实经验与过往记忆之间的耐心追溯和捕捞,为当代青年男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流动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形态。
在《夜樱》里,来到山洪暴雨后小镇的她,在倾听爱人的诉说之后,默默吞咽身世过往的艰涩处,决定与之分手。《奥德赛之妻》中,面对在天台上讲述爱情的女学生,关于英雄奥德赛与其妻子佩涅罗佩、情人卡吕普索关系的重新思考,也牵动起戏剧导演萧鼐的前尘往事与当下情感状态的抉择。
《面具》里她叫他R,她喃喃自语,记录与他有关的一切,她诉说爱意,但字句之间充满了犹疑,她把自己与R的情感比作卡夫卡与菲利斯,她提问:人到底从何获得一种观念与自信,相信可以凭借书信来彼此交流。《江洲月》从“我”的视角看出去的阿丹、阿香这些女孩子的故事,她们年少辍学,洗过盘子砸过碗,在工厂里打过工,在美容院过上了尚且安定的生活,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有时突然觉察青春易逝,有人养着男友,也有人嫁了,夫妻吵架并不比其他夫妇更多,日子终归过得去的。
《四季歌》写一对对青年男女关于记忆和日常经验,恋人之间的相处既暗含着平静的失望,也在有限的诉说和袒露之中暗自等待着的空谷足音。
《洄游》和《移民》里,关于海岛上的沉船事故、海外富商的新闻报道与繁芜的现实生活状态之间构成了某种微妙的错置感……
这些小说描写了女性的际遇,但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类为女性主义小说。《洄游》和《四季歌》都从男性视角讲故事,《夜樱》起笔,从阿杰讲到医生再引出女主人公,《奥德赛的妻子》从戏剧导演萧鼐起笔,以经典文学《奥德赛》对应现实里的女性人物故事。另外几部小说的男性形象即便是侧写,依然鲜明。这部小说集并不需要刻意强调女性特征,因为它本身就是关于“关系”的探索,而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不分性别的组合联结。
小说中的人物一直不断移动,在不同的城市迁徙,但他们选择落脚的地方,多多少少是一些边远的“小镇式”地方,而回到或去往这些边远的地方,都是主人公自己主动选择的。小说里的移动不是出逃,是一种追寻或者说一种求索,很多人物都经历了这种“启程—抵达—难熬—再出发”的结构。
《夜樱与四季》比起《嫉妒》进步了很多,手法更加多样化。比如,叙事者视角的转化。第二人称“你”通常很少用于小说创作,这个叙事角度有利于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描写。《夜樱》的视角从“他”到“她”到“你”,“他”和“她”的故事告一段落,接着就开启了“你”和“她”的故事。
人生就是如此,当一段故事进入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生命将建立新的联系。张玲玲尝试在小说创作里,更多体现这些联系。
文本中的有些小说带着作者身为记者职业敏感性,把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制度的、宏观的方面结合起来。《移民》是最具自传色彩的作品。一个女记者参加了稻盛和夫的演讲,旁边座位上是一位深深折服于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女企业家,女记者倾听了女企业家的拼搏经历,接着赶赴约好的访谈,另一位具有真真假假“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在女记者的感觉里,他的故事已经打磨过多遍,重要的不是真实与否,而是故事的结构与叙述方式。女记者困惑于职业所谓的“求真性”。
张玲玲的写作关注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在《夜樱与四季》后记,张玲玲自述,都市情感故事并非她的旨趣所在,小说的动因始终是“爱”而非“爱情”,还包括对于个人幸福、历史记忆的探查和思考。
社会化的运作机制是如何一点点挤入个人与个人之间,不断瓦解又不断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呢?我认为,这才是张玲玲作品的真正内核。